本帖最后由 江边听风 于 2011-6-21 10:00 编辑
华阳,安徽望江县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老镇,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北岸,位于九江和安庆这两个地理要冲中间。原来的华阳老街,建有一个水运码头,在明清时期,因望江以及周边的宿松、太湖、潜山四县北面背靠绵延的大别山,与外界相通的通道,就只能依托这个水运码头南出苏杭湖广,所以显得相当的繁荣和有名,不少的诗人在此留下赞美的诗句。由于长江的崩岸和涨滩,风光了几百年的华阳老码头无法停泊船只,新中国成立后,为适应客运和物资运输的需要,将码头上移五公里,建到一个叫“江调(读tiaou)”的小圩里,港口的名称仍叫“华阳”,其实码头与华阳的镇区隔着五公里的路程。久而久之,“江调”的地名,在人们的口语习惯里,就被码头取代了。 那时候的水路船运,是重要的交通工具,更是四个县远行的唯一选择。长江里的客运船只归属“长江航运公司”,总部在汉口。以汉口为界,将上海至重庆的整个航程分成“上海--汉口”和“汉口--重庆”两个部分。长途客运航行的轮船比较大,一般有四、五层高,习惯上叫“大轮”,区间航行的客运轮船比较小,一般只有三层,习惯上叫“小轮”,新建的华阳码头是停靠大轮的,所以又叫“大轮码头”。一般来说,“大轮码头”只建在中型以上的城市,整个长江航线,唯一一个农村的小码头停靠大轮的,只有这里的华阳港。 华阳大轮码头大约是一九六五年建成通航的,这对我们这些大轮码头周围的人来说,是一件欢呼雀跃的大事,更是一件引为自豪的大事,这种自豪感一直延续了好多年,江调圩的人出门在外,都很自豪的自称“码头人”。 开始的时候,江里跑的大轮,以“江”字开头命名,我能够记得的有“江汉”“江亚”“江申”“江平”“江渝”等等,据说这些轮船都是解放后,通过公私合营从资本家手里接管过来的。我们村里好多人,都能够准确的推算出今天是什么名字的大轮上水,什么名字的大轮下水,因为从这里上水到汉口,下水到上海,差不多的时间,都是两天。这些轮船的名字叫了不太长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所有大轮的名字都改成了“东方红”的系列编号,从此,就称为“东方红1号”“东方红2号”“东方红3号”等等。 华阳大轮码头除了停靠大轮外,还停靠小轮,属于安庆到九江航线上的一个站。后来还加有一条华阳到扬湾的专门航线,这样,每天停靠的大小轮,上下水加一起,最多的时候也有六个班次。 上水大轮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到,相当准时。抵达港口的时候,拉响一个长长的鸣笛,我们那里的人叫做“大轮拉位子”。那时候农村家庭里很少有闹钟,更谈不上有手表了。“大轮拉位子”是一个很好的计时工具,提示老太太们:该烧午饭了。下水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,再能熬夜的人,一听到下水大轮拉位子,都赶紧的收拾睡觉(那时候人劳动强度大,睡觉早)。 有码头自然就有港务站。港务站有十几名工作人员,主要包括售票、验票和趸船上的水手。没多长时间,这些人都与我们村里的人混得很熟,村里有红白喜事,也都请他们来做客,关系要好的,过年的时候还互相串门。这里面于我印象最深的有老杜、老贾和小杨。老杜定格在我的印象里的是:操一口唱戏一样的口音(后来知道是宜昌人),戴一顶灰尼圆帽,抽一口自己卷的黑古溜丘的粗大卷烟。他卷烟的纸是专门用来卷烟的雪茄色专用卷烟纸,烟丝也比我们这儿老农常抽的“黄烟”粗短,这让人很好奇(我们当地人偶尔也卷烟抽,用的都是废报纸或者小孩用过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)。更让人好奇是,他能在高兴的时候,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,变戏法一样,变出几个水果糖来发给小孩,那时候的小孩一年都吃不到几次水果糖。 小杨来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小,有三十多岁了,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,侉气、豁达、和善.他们自己人喊“小杨”,村里人也就跟着喊,有时小孩子见面也这样喊,他也乐哈哈的答应,还伸手在鼻子上刮一下,能被“小杨”刮一下鼻子,大家都很乐意。 老贾不爱说话,但人非常友好,农村人找他什么事,从来没有架子,只要能办到,他都不声不响的给你办。这些人的子女也在我们村里的学校读书,老贾的女儿就跟我是同班同学。 候船室是最热闹的地方,也是那个年代我能见到的最好最宏伟的建筑,石头的墙基有一人多高,水泥钩的缝,红砖红瓦,一排溜的玻璃大窗,显得大气磅礴。晚上,许多盏高功率的白枳灯,把宽敞的大厅照得透亮。 大厅周围的木长条椅子上,坐着各色的行人,这些人的装束与我们村里人是完全不一样,我们村里人过年都穿不到这么好的衣服。得空到候船室看来自各地的人流,是一道很不错的风景。同样能看人群风景的,还可以在每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,上水大轮靠岸,从船上下来来自上海、南京、芜湖这些大城市的旅客。他们的衣着、发式、包裹,甚至走路的姿势,都是观赏和过后评论的话题。可惜,这个时间能够观赏的只要老人和小孩,爱热闹的小姑娘小伙子,只能在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才能来。 船快到的时候,候船室的高音喇叭,不时的播放请旅客准备上船的提示,播音的普通话很动听,比我们老师的普通话都好(至少我们当时是这么认为的),从每天差不多一样的播音里,我们知道,在我们的上游,有九江、黄石、武穴、汉口。在我们的下游,有安庆、池州、铜陵、芜湖、马鞍山、南京、镇江、南通、上海。 上船的铁匝门口,工作人员拿着手持的扩音器,反复的喊着地名,我们一班小学生喜欢学,放学的路上,拿练习本卷着当话筒,一路走一路喊:“马当、彭泽、复兴、红光、湖口的旅客,收拾好行李,准备上船了呃”。话未的“呃”到我们嘴里,就夸张的叫得特别响。 在码头上游二十公里,有一个大型的国营农场,这个农场的性质不断的变换,随着它的变换,码头人流的风景也不断的变换。一开始是劳改农场,关押着主要是华东地区的犯人,以上海人为多,这时码头的人流就大多是探监的家属。“文革”期间改成农恳农场,里面全是下放的知青,码头的风景立刻变成知青的海洋,这是码头风景最靓丽的时期,“文革”结束后,又改成劳改农场,从船上下来的,多是本省马鞍山、芜湖、池州的探监家属,以芜湖为主。芜湖是一个很前卫的城市,其发型、衣着、服饰,总是领导新潮流,对码头姑娘小伙影响不小。 码头的夜晚,是码头人休闲的必然处所,尤其是夏天。 劳累了一天的农人,吃过晚饭,大都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,摇着芭蕉扇,海阔天空的闲聊,姑娘小伙及精力过剩者,则三两结伴来到码头,沿着江堤,享受着清凉习习的夏日江风。过往船只的红灯绿火,融化在波涛滚滚的江面,如同绚丽的霓虹,映衬在江对面起伏山峦的黑山墨影之中,令人陶醉,催人往返。 部分与码头工作人员特别熟悉的,还可以登上趸船,等待下水大轮的到来,近距离的看看水面上跑着的庞然大物的模样。没有机会乘坐一回,看一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就像没有坐过飞机,能到飞机边上看看也好。 刚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,停泊在货码头的货船上每晚都可以看电视,这真是很美很新奇的事,不过家里不让每天去.走跳板上船危险.我第一次看电视,就是在驳船上看的<<难忘的战斗>>,一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片。后来,又连续在驳船上看了毛主席逝世的新闻. 有了码头,就有了客流,自然就有了配套的部门。印象里的部门有:饭店、旅社、百货公司、邮政局、派出所、卫生院、食品站、遣送站、农机站、搬运站、农资公司、煤建公司等等,有了这么多部门,俨然就是小有规模的集镇了。 六九到七三年,我那时上小学,每天路过码头,印象最深的是码头饭店。饭店的馒头和肉包子非常好吃,馒头是二两粮票五分钱一个,肉包子是一两粮票八分钱一个。生产队有时兴致来了,拿米去换,二两米一个馒头,换回来分给社员,社员拿回家一家老小一起吃,小孩子一片一片的撕着,慢慢的嚼,细细的咽,一个馒头要吃半小时。这也算是一年次把次的加餐解馋吧。肉包子味道更美,浓浓的、油油的汤汁,细滑的、香嫩的精肉,吃完了两三天还在回味。我们小孩吃包子从边上的面皮吃起,汤汁流到手上,要在手上舔半天,到最后才舍得吃中间的肉馅。有一次舍不得吃的肉馅,舔手指的时候一不留神掉了,对着地上的肉馅看半天,半个月都在懊恼。后来我吃过无数的包子,虾仁蟹蟥乃至鲍鱼馅的我都吃过,却始终找不到当年那肉包子的感觉。 码头的饭店最诱人但又最怕人,每每走过都绕着走开,免得馋人。最好玩的是邮电局,邮电局长途电话的机房最值得玩味,耳机夹在头上,细细的话筒伸到嘴边,像打仗的电影里发电报一样,不停的把电线插来插去,手上死劲的摇,嘴上喂喂的喊,一番捣咕半天,接线员拖着长音喊一声“来—了”,打电话的人就可以与对方通话了。接线员里印象最深的是老赵,瘦瘦的,一口慢吞吞的怀宁口音。那时候邮电局的人绿衣绿帽,骑绿自行车,车的大杆上还有一个绿色的大袋子,出门很神气。 大轮从遥远的大上海来。那时候的上海,在人们的眼里,向往得如同人间天堂,出门提一个印有上海二十四层锦江饭店标志的包,都是最时髦的物件。码头人可以通过趸船上的工作人员,买到上海的生活日用品。最先的是香烟。谁家要是计划要办喜事,早早就打好招呼,买上几条“勇士”“大前门”“飞马”牌香烟,做喜事的时候甩出来,非常有面子,花的钱还不多。后来就有带毛线的,红的、绿的、灰的,又便宜又好,把码头以外的人嫉妒得要死。 让人嫉妒的还不仅仅如此。那时候农民的收入,每户每年能卖一头自养的猪(极少数人家卖两头),有个百十块钱的进项,剩下的就完全依靠年底的工分分红。一家老小全年的支出就指望它了,油盐柴米、衣食住行、生小养老、来情往礼甚至打针吃药,等等的一切,全都在这里。人口多工分少的超支户,年底根本没有分红,有的地方不超支的也没有分红(分红的钱被超支户挤占了),因此日常的消费来源非常困难,以至学生买一支铅笔的三分钱都拿不出来,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。 相比之下,码头的人经济上就活咯得多了。 “江调”这个地方盛产花生,知青回家过年的时候,大包小包的买了带回家。生的干花生是五角钱一斤,现在的熟花生也只有三块钱,比较起来,那时候的五角一斤,是非常不错的价钱,当然是码头人一个不错的经济收入来源。 如果你有经济眼光,在候船室里,你还可以零卖炒熟了的花生、煮熟的红薯、嫩玉米、菱角等等,在那个年代,有这些经济补充,是非常难得的,当然,你得偷偷的去干,小心割资本主义尾巴。 除了有大小客轮外,码头还有货运功能,主要是运进来的煤炭和运出去的棉花,上下货的搬运自然由码头人来做,为此,村里(那时候叫大队)专门成立了搬运站,各生产队轮流派人,活计虽是重了点,收入还是可观的,在搬运站干一天的收入,要抵在生产队干四五天,而且还是按月兑现的现炒。 货运码头停的货船,常规的停有三五只,码头那么多的机关单位,这些人吃的菜,基本由码头附近的农民供应,卖菜成了解决零用钱来源的又一重要渠道。鸡下的蛋,一般人家是很少舍得吃的,七分钱一个的都拿来卖了。 对于码头附近的村民来说,码头真是一个好地方,外面的姑娘愿意嫁过来,里面的姑娘不想嫁出去。 大轮码头的风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,期间人们出行,搞一张四等舱的船票都还要托人找关系,前面说的小扬的儿子,后来当了站长,他是我弟弟的同学,我就常常通过他买票。 进入本世纪,就慢慢衰微了。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,汽车的快速便捷,取代了速度缓慢的轮船,坐轮船的人就越来越少。到二00五年,长江的轮船航线全部停运,大轮码头作为单一的功能失去了存在的依托,配套的机构也相继撤离,昔日繁荣的风光不在,只留下大门紧闭的空房子。有的房子被附近的村民买下改作他用,有的房子仅以地皮的价格变卖后建了新的房子,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摸样。当年最宏伟、再热闹的候船室、饭店,则任由雨打风吹去,墙损皮剥、门窗残破,空留风烛残年的轮廓。 从一九六五年到二00五年,整整四十年。上年纪的码头人每每说起,只有伤感的叹惜。
这是进出码头的公路
这是这是当年的东方红饭店,落败的面目里还隐藏往日的富丽堂皇,带着陈年的记忆,还能闻到诱人的肉包子香味吗?
这是当年的东方红旅社,两层楼的建筑,是大轮码头早期最高的楼房,石头砌驳水泥勾缝的墙脚,坚固而华贵。无奈岁月的变迁,落了个垃圾横陈境地,无颜回首曾经的风光。
上船的通道
当年的百货公司,虽不是琳琅满目,但也是很吸引眼球的,进门右边卖布匹,左边卖日杂。
当年雄伟壮观的标志性建筑——侯船室,只有门头上航运公司的标志清晰可见,曾经的喧闹已经不复存在,被随心所欲的搭建和啼笑皆非的广告牌肢解得面目全非,如同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凄惨的流落在无人的荒野。
农资公司办公室兼职工宿舍
这一张旧船票,已经无法登上记忆里的客船 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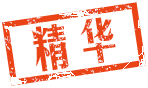
 |Archiver|手机客户端|皖公网安备34082702340930号|望江论坛
( 皖ICP备18018829号 )
|Archiver|手机客户端|皖公网安备34082702340930号|望江论坛
( 皖ICP备18018829号 )